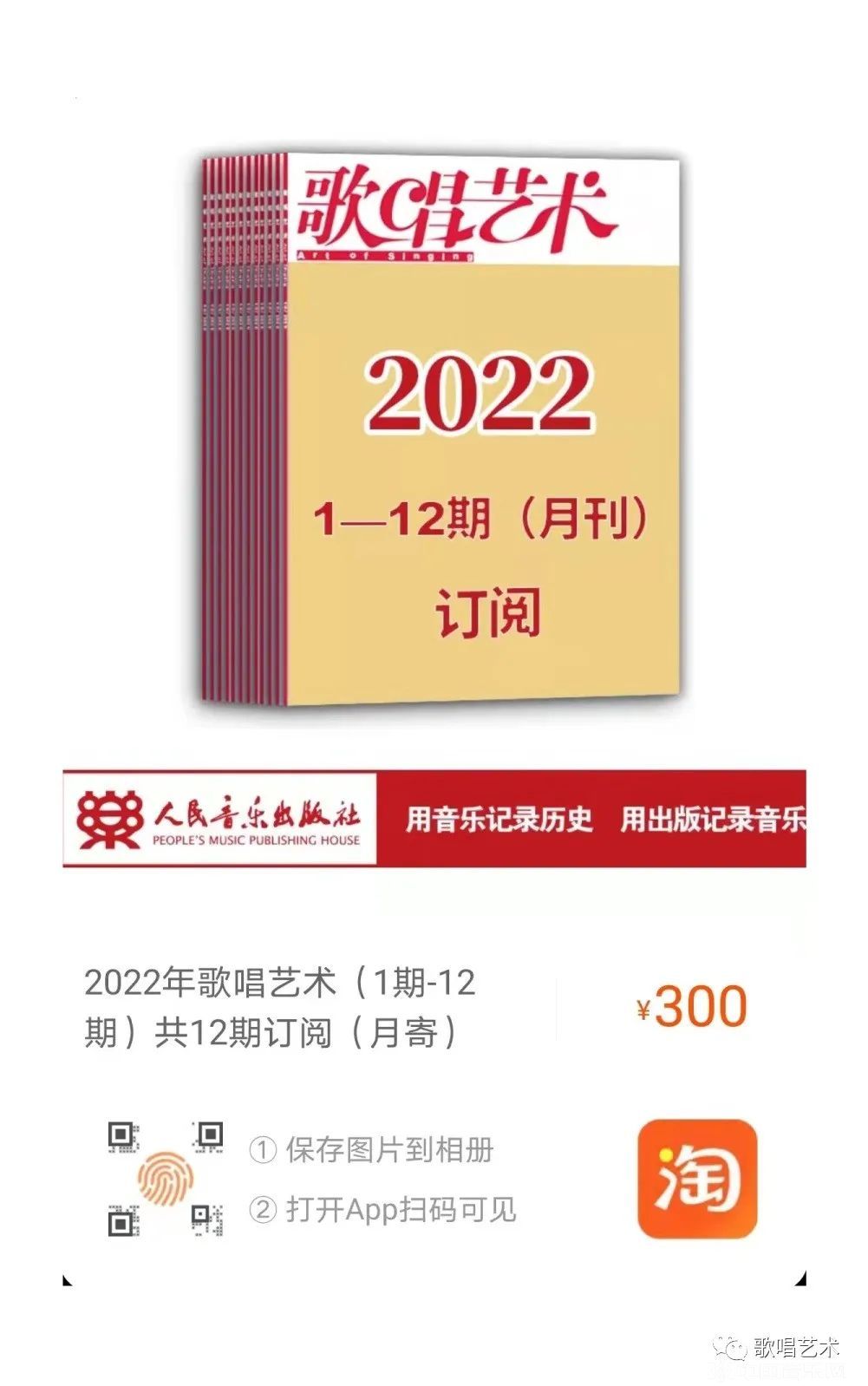陪伴歌者——和邓垚老师聊钢琴伴奏
原文刊载于《歌唱艺术》2022年第3期
访谈者
俞子正,男高音歌唱家,《歌唱艺术》常务副主编。
嘉宾
邓 垚
钢琴家,作曲家,中国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2003—2005年,连续三届荣获“中国音乐金钟奖”之“全国最佳伴奏奖”。2007年,荣获“中国音乐金钟奖”之“特殊贡献奖”。2012年,荣获文化部“第十届全国声乐比赛”之“钢琴艺术指导奖”。

俞
邓垚好!好久不见,出于疫情的原因,演出和比赛少了,所以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邓:是啊,但是您说要和我在《歌唱艺术》上聊聊,我很高兴,也确实有很多话可以和学习声乐的朋友们聊聊。
俞
您现在很“火”,几乎所有上规格的比赛和演出都有您的身影,很多歌者都非常崇拜您。有歌手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邓垚老师弹一次伴奏,此生无悔,您感觉如何?
邓:我不敢用“火”这个字。实际上,钢琴伴奏这个职业,我觉得是服务性行业的典型代表,我就是为大家服务的。一些上规格的比赛和演出都有我,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需要我。更多大家没看到的,一些小规模的比赛和演出,我也在。比如说,我也经常为考学的孩子们弹伴奏,而一些程度比较差的孩子,我也愿意尽我所能地为他们服务。我觉得钢琴伴奏,首先就是要陪伴,这些孩子从声乐爱好者到最后成为歌唱家,慢慢地陪伴他们的这个过程,让他们能成才。所以,我不能叫自己艺术指导,我其实就是一个踏踏实实的钢琴伴奏,从点点滴滴做起,陪伴歌者、陪伴教师、陪伴未来的歌唱家。于我而言,我希望以后更多的就是陪伴,陪伴中国声乐的发展时间长一些,期待他走向世界。
俞
现在很多人自诩为“艺术指导”(coach),有些人伴奏弹得一塌糊涂,也说自己是艺术指导。一夜之间,“钢琴伴奏”纷纷摇身一变,成了艺术的“指导者”。我听您还是说自己是钢琴伴奏,您是谦虚呢?还是……
邓:说到艺术指导,我觉得首先要加上“钢琴”两个字,钢琴伴奏最多能叫“钢琴艺术指导”,但是为什么很多人都管自己叫“艺术指导”呢?这可能是借鉴了国外歌剧界、声乐界的惯例。因为,在国外的艺术指导,他们被统称为艺术指导,实际上已经超越了钢琴伴奏。尤其像国外的歌剧艺术指导,简直太棒了,他们不仅能弹能挥,自己还能唱,所以它包含了语言,像德语、意大利语、法语等;再加上歌剧的角色、内心、对白,在合乐队之前都给走台了,艺术指导是这么一个角色。我们现在统称的艺术指导,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名词而统一过来。那么,目前我们能不能做到艺术指导呢?实际上,是不能的。我并不是谦虚,因为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钢琴伴奏,在某些歌上,我可以给学生一些指导,所以最多只能叫做钢琴艺术指导。我并不能做到像咬字、外语,或者更全面的一些指导。所以,我认为钢琴伴奏就是钢琴伴奏,服从于主课教师,不能越位,既不能讲得太多,也不能不讲。因为声乐教师是宏观的,他们对学生的发展有较全面的计划,一年级唱什么歌,二年级唱什么歌,直到五年级。有时候我确实好心,可能对一年级的孩子讲了五年级的概念,他们反而不会唱了,所以应该慢慢来啊。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本色”问题,一点点地配合主课教师,把主课教师对孩子的期待,或者他想让孩子在什么程度呈现什么样的作品去完成好。
俞
我在很多比赛和演出中看到您确实很忙,但是您又创作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您觉得创作和演出之间有什么联系?譬如,通过演出可以知道大家喜欢什么样的风格,您是投其所好,还是坚持自己的个性、自己的音乐语言,使得大家都喜欢您的作品?
邓:确实忙,所以我并不是职业创作的,有时候一首歌要构思很长时间才下笔。比如说,这段时间我想给张群航写一首歌,词的灵感是电视剧《甄嬛传》里一个诀别书的词,我希望能写一段属于张群航的古诗词歌曲,所以我也在思考,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有句古话,“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弹了很多的伴奏,我也从其中汲取了很多营养,在创作的时候就特别有帮助。虽然我本身是学作曲的,但是现在的职业是钢琴伴奏。我是这么定位的—职业是钢琴伴奏,事业是作曲。我一生都会给大家弹伴奏,但是我的目标还是能写出更好的歌,希望大家喜欢。至于风格,我在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风格,通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和感知,对某个风格比较喜欢,我就进行创作,并没有固定模式。关于我的音乐语言,相对来说,我认为自己从2008年开始写了两首新歌至今,我的音乐语言就是偏通俗、流行,因为中国声乐在进步,演唱在进步,所以中国声乐作品的创作在进步,钢琴伴奏也在进步。现在的伴奏带都已经非常“流行”了,非常与时俱进了,包括钢琴伴奏的织体和语言。“抖音”经常有人说我弹琴有点儿“垚里垚气”的,这个可能有褒义也有贬义,但是我觉得也挺合适,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感知。
俞
我也关注到您出现在民族声乐赛场比较多,相比之下,“美声”赛场可能少一些,也许是我在“美声”赛场当评委,太期待您出现了。那么,您跟那么多民族声乐歌唱家和选手合作,您对目前民族声乐作品的创作水平有怎样的评价?从作曲专业角度说说。
邓:这个我可以“凡尔赛”一下,为什么呢?“美声”我也弹,但是后来确实民族声乐弹得太多了。以前,“金钟奖”是“民族”“美声”“流行”一起比,所以“流行”我也弹。比如说,我弹的“流行”(歌手)获金奖的有周强,就是现在火箭军政治部工作部文工团的周强。我弹的“美声”获金奖的有杨阳,真可惜,他已经不在了。我其实弹过很多,包括戴玉强老师等。后来,“金钟奖”比赛就分开了,“美声”是“美声”,“民族”是“民族”,“流行”还拿出去比,所以我就没法都弹了。那我弹的比较多的是“民族”,我就固定在“民族”场地弹了,如果两个场地同时比,我也串不开场。至于“美声”的钢琴伴奏,我觉得首先要尊重原谱,尤其是艺术歌曲,德奥艺术歌曲。歌剧也是这样,必须严谨。比如说,弹莫扎特的歌剧选段,必须要尊重当时的年代感,风格必须要统一。至于对民族声乐作品的评价,我觉得就是既要传承,又要创新,我内心其实是有一个模板吧。我也有自己的偶像,比如说,赵季平老师,就是既要好听,又要有民族性。我那会儿要考赵季平老师的博士,后来因为他身体不好,那年就没考。其实在2003年,王梦洁老师和李双江老师作为见证人,我跪地磕头,敬茶拜了赵季平老师为干爹。但我并没有拜师父,为什么?因为我个人更崇拜他,所以也想孝敬他。他就是我的榜样和模板,他写的这种音乐,像“新三国”,每次听起来都耳目一新。实际上,我最早的创作灵感很多都是他给予的。我认为民族声乐作品首先还是要有民族性,但也要接轨现在的流行音乐,包括大家爱听的,因为还有广大的受众群体。
俞
我听您的伴奏,之所以让那么多歌唱家和选手喜欢,当然,首先是您人品好、专业好。其次,在技术上,您能够给歌者更多的情绪依托,也比较熟悉歌者的呼吸和乐句。学习声乐的人和学习器乐的人不同,读谱常常不严谨,有时候很自由,甚至“自由化”,所以弹声乐伴奏不太容易。我听您伴奏里有很多即兴的成分,包括音型的变化、和声的变化,是根据歌者的情况做出的补救,还是根据您自己的爱好事先设计好的?
邓:哈哈,人品好是必须的。我又要说到服务性行业了,因为钢琴伴奏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你必须得人品好,要配合,是永远的绿叶。那么,您说到是不是根据歌者的情况做出的补救呢?实际上,我不是要根据歌者的能力去做变化,我会在之前有大概的设计。在合伴奏的时候,我已经为这个歌者量身定做了钢琴伴奏,调整和即兴也都是提前设计过的,不是真的即兴。如果是考生,相对来说,我会注意简单一点,或者哪怕我特别即兴的右手给旋律,这也是为了考生,为了他们的音准。比赛又有比赛的考虑,这都是要提前跟歌者沟通。举个例子,《敕勒歌》中间的转调,我一定要先把调转过去,再让歌者张嘴唱,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把调转好了,再张嘴唱就不会跑调。如果只是为了有效果,就应该间奏不转调,这样处理会有意外的效果,但是所有的处理都跟歌者提前商量过了。所有的变化、所有的自由都是提前设计好的,我并不能绝对的自由。个别音,某些音,有没有即兴的成分呢?有!但整体布局是必须提前思考的。所以很多人说,听邓老师弹琴,可能是即兴弹的,但听起来却比正谱好。这个问题,我一点儿都不含糊,绝对弹得是比正谱好,简单、有效果,这就是我一直追求的。我觉得这也跟作曲(功底)分不开。因为学了配器,我会更全面地考虑音乐的整体效果。因为学了复调,我能够更好地处理声部间的呼应。因为学了和声,我能够让歌曲的和声色彩更丰富。因为学了曲式,我对歌曲的结构有了更宏观的把握。我所考虑的不仅仅是一首歌,有时比赛可能要唱两三首,考研要唱四首。有时要弹音乐会,得整体布局,才能引人入胜,才能让听众慢慢地、静静地听歌者唱下去、听我弹下去,什么时候是铺垫,什么时候是高潮,什么时候要满足你所有的审美体验。
俞
我在“抖音”上经常关注您的动态,您的短视频里有许多很有趣的场面,譬如“钓鱼要到岛上钓”“终于练成了用意念翻谱子的功力”,等等。可以看出,您是一个快乐的人,一个勤劳的人,一个有趣的人,一个浪漫激情的人。而听您伴奏的音型、和声色彩,您是一个内心丰富的人,我非常喜欢!那么,您觉得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邓: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呢?对我来讲,最大的乐趣是吃,我非常喜欢美食。我全国各地去过不少地方,但是让我说风景名胜,我真的记不住,但可以问我去哪儿吃。我觉得我首先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因为爱吃;其次,就是音乐家一定都是美食家。因为我自己在不忙的时候,也会烧烧菜、做做饭。这跟创作是有相通之处的,也有灵感。所以我经常说吃过的好吃的,我一定要能自己也能做出来。
俞
哈哈,这个我有同感,对于人生来说,吃喝都马马虎虎,那还能“乐业”吗?我有些朋友喜欢关在家里“做学问”,对吃喝没有要求,粗茶淡饭,比较简单,而不是精致。偶尔相聚,也是只谈学术,即使笑,也不会畅怀大笑,真的很让人佩服他们是如何坚持成了习惯的。您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有开心也有失落,有温暖也有伤感。现在我们来谈谈您的学习经历,是一帆风顺的,还是经历磨难的?
邓:我是1991年上的中国音乐学院附中,1994年上的大学,一直学的是作曲专业。学习上来讲,我也没有太受什么磨难,只不过就是在选择工作上。大学毕业以后,我虽然是搞创作,但是一个作曲系的本科生的确不好找工作,所以我就选择去文工团弹钢琴伴奏。弹了20年钢琴伴奏,得到大家的肯定,同时也写歌。后来这个文工团解散了,我现在又来到了中国音乐学院。我还是很知足的,因为我觉得始终是为大家服务,大家需要我啊。不管是弹伴奏还是写歌,只要大家喜欢,我就愿意一直这样下去,为更多的人服务。
俞
中国声乐界大部分“名家”,您都合作过,我觉得您无形中成了钢琴伴奏这个专业中的榜样或者说是标杆。您也许谦虚、不承认,但事实如此。作为一个榜样,您想对全国的钢琴伴奏同行说点什么?
邓:不能说自己是榜样,我只能说我争取做一个中国声乐、民族声乐的领头羊吧。真的不能说是榜样,我只是想给大家多一些在音乐上的思考。我1992年开始从附中弹伴奏至今,30个年头。起初,我也没想到,通过自己能改变民族声乐的一些理念、观点、表现手法,包括大家的听觉。实际上,大家的听觉这么多年还是略有改变的,也很接受这种相对有一些变化的、比较新颖的钢琴伴奏的和声和织体了,我想一直努力下去。很多人都说,邓老师,你怎么不多写点歌、多配点器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很多这种创作灵感都来自钢琴伴奏,所以我要多弹点儿。我要跟我的同行说什么呢?要大量地积累曲目,首先要多弹。我也慢慢开始带研究生了,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带博士。我理想中的钢琴艺术指导这个专业方向就应该是全能的,但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中国歌、外国歌都能弹,包括流行、音乐剧,这是一个钢琴艺术指导全面发展的方向,但又术业有专攻。比如说,跟我们佳林老师多切磋,张老师的“美声”作品弹得好。所以,我们要成立艺术指导学会,当然这也是愿望啊。然后,给广大的钢琴伴奏者普及一下“美声”钢琴伴奏、民族声乐钢琴伴奏,也多普及即兴钢琴伴奏。在中国音乐学院,以龚荆忆老师为带头人,还有我和任卓。任卓主要讲中国歌剧的钢琴伴奏,龚荆忆老师主要讲中国艺术歌曲的处理,我主要讲即兴伴奏。我们仨是个小团队,也去过很多学校讲学,特别受欢迎。因为我们的侧重点不一样,又都是围绕中国声乐。我要说的就是任重而道远,希望大家整体提高,团结一心,为更多的人服务。钢琴伴奏其实是这么多年并不被特别重视的一个艺术行当,近两年可能稍微好一点了。所以我们要努力,大家不仅要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还要提高服务水平,让大家既重视我们,又欣赏我们。
俞
我们在舞台上和“抖音”里看到的您总是快乐的,您有烦恼吗?是什么?
邓:我没有太多的烦恼,我的烦恼其实跟大家都一样,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就是孩子,我的孩子也要考学,也要学习,也就是生活上一些简简单单的烦恼。在专业上,我是没有烦恼的,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取得更多的好成绩。比如说,“金钟奖”能不能每届多设定十个金奖之类的,我希望我弹的选手都能获得金奖,这就是我的“烦恼”。在舞台和“抖音”里,我是快乐的,我想让我的快乐感染更多的人。十分感谢俞老师给我这个机会,虽然这个采访,我的回答可能有点儿简单,但是我说的都是真话。我特别喜欢跟您多请教,跟您多聊天,有机会希望咱们见面再聊聊。
俞
谢谢您!和您聊天很舒畅,您说的都是实话、真话,没有一些“大师”说得挺吓人但又吓不到人的虚话、大话和胡话。而且,我们看到了一个在舞台下真实的邓垚,也给我一些启发。譬如说,我们是否应该对目前的钢琴伴奏课程和作曲课程进行一些反思呢?如何把研究、学习和实际运用更好地结合呢?所以我想,今天的采访会引发全国的钢琴伴奏者和声乐学习者很多思考,我们还会在舞台上和“抖音”上感受您热情洋溢的“垚里垚气”。
购买本期纸质期刊,请登录淘宝网“人民音乐出版社”天猫旗舰店进行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