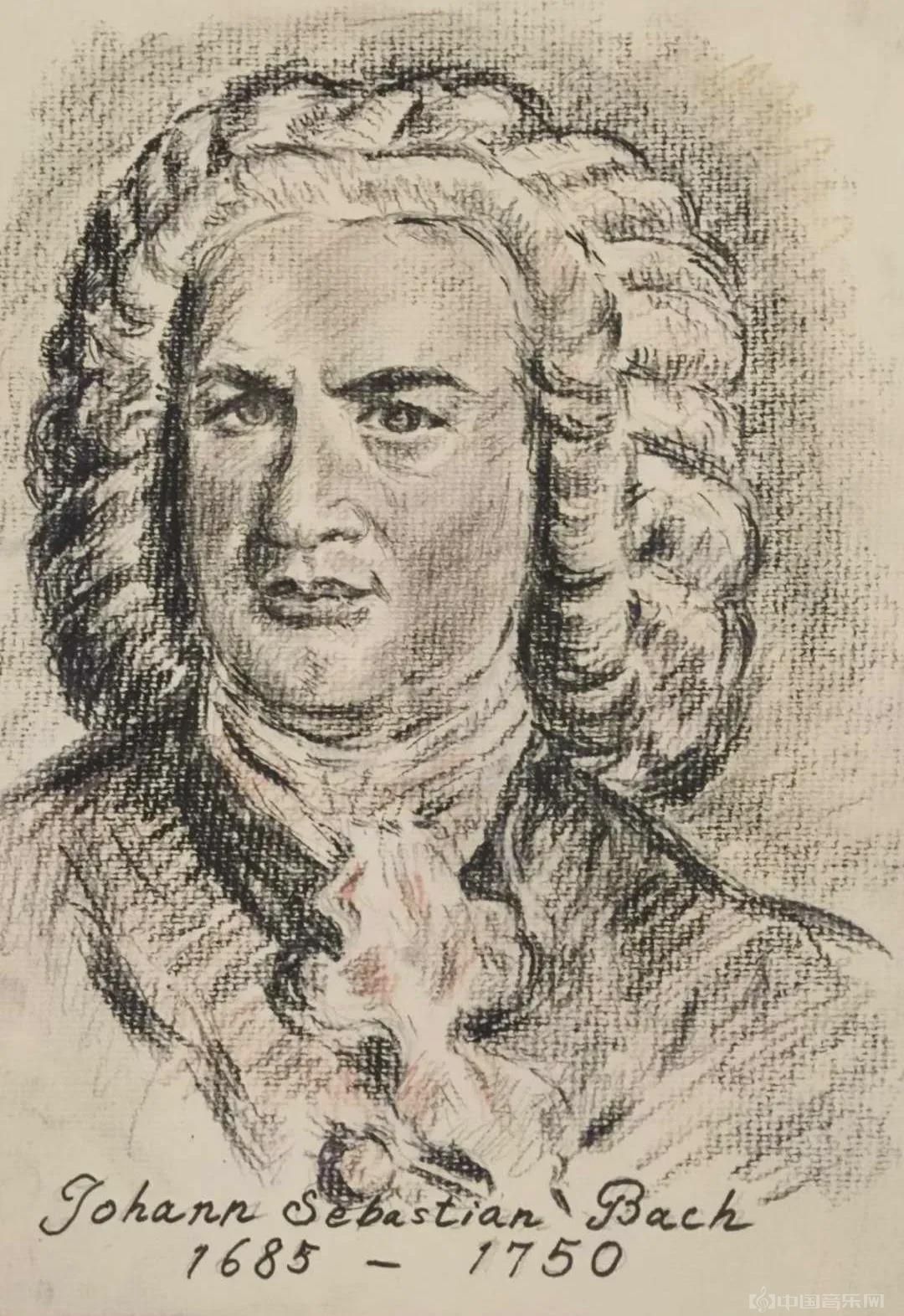文 | 张硕
“我小时候兴趣广泛,看书、画画、滑冰样样喜欢,其中最喜欢的就是画画。上课的时候,我把每本书的边角都画上手持刀枪剑戟的小人儿,只要把书角一捻,这些小人儿就手舞足蹈地打起仗来。有时候,我在稍微硬一点的纸上画上漂亮的女孩子,再剪下来;再在软一点的纸上画各种衣服、裙子、鞋子、帽子、皮包;涂上漂亮的颜色,剪下来就成了可以随时给小人儿换穿的时装。我画的小人儿和衣服可以装好几盒呢。”如今,年届八十的钢琴家鲍蕙荞,回想起小时候制作的那些“活动电影”和“纸壳娃娃”,仍然笑得像个孩子。
“我这辈子,有太多事都是‘无心插柳’。”鲍蕙荞说,如果不是机缘巧合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她说不定会成为画家,或者服装设计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鲍蕙荞倾听同行——中外钢琴家访谈录》是始于1999年的又一个“无心插柳”之作。不久前,《倾听同行》第四集出版发行。22年前无心插下的“柳”,如今又得到了一片绿荫。
《倾听同行》具有
1999年,应《钢琴艺术》邀约,鲍蕙荞采访了她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习时的主科老师陈比纲教授。这次访谈获得了空前的关注,杂志也有意请鲍蕙荞继续对一些同行和老
“我可能比记者们多了一点优势,就是能在各种场合和同行们碰面,大部分的受访者都是我的老朋友,也因此我们能聊得更加深入。”鲍蕙荞说,多数的采访都是在活动的休息室完成的。虽然采访之前她会提前准备好提纲,但她从不把问题提前透露给受访者,“这种‘没有准备’的回答,反倒能更真实地把一个人平时思考的问题,从深层次的思维里‘调’出来。”在写作中,鲍蕙荞力求最大化地还原现场对谈,以此突出受访者的性格特征。此外,书中还加入了受访者的简介,还有鲍蕙荞对受访者的印象、相识之初的故事、访谈的机缘等,力求让每个受访者的形象更加生动立体。正如钢琴家周广仁所说,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中国钢琴界的历史,了解世界知名钢琴家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奋斗精神,鲍蕙荞做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程”。
没有演出和录音的日子,鲍蕙荞偶

鲍蕙荞为作曲家鲍元恺画的肖像
鲍蕙荞画的巴赫像
48小时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六七岁的时候,鲍蕙荞离开了出生地四川和住了不到一年的上海,定居北京,爸爸花了100元大洋为妈妈买了一架带有铜烛台的老德国钢琴。但是鲍蕙荞并没有开始学琴,只是边玩边听着妈妈弹奏《献给爱丽丝》《少女的祈祷》《多瑙河之波》。直到9岁的暑假,妈妈突然决定教哥哥和鲍蕙荞弹琴。从《汤普森现代钢琴教程》学起,她没几天就“开了窍”,后来妈妈怕自己仅有的知识限制她的进步,就辗转给她找了一位波兰来的名叫帕夫洛夫斯基的老师。在帕先生之后,鲍蕙荞还先后跟随过几位老师。“那几年我虽然喜欢弹琴,进步也很快,却从没认真想过要当一个钢琴家,时而想当作家,时而想当画家,时而想当乌兰诺娃(芭蕾舞演员),又时而想做米丘林(生物学家)。”
直到13岁那年暑假,一个朋友告诉鲍蕙荞,她已经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改名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并已通过了专业考试,第二天就要去考文化课了。鲍蕙荞一听急得不行,“我怎么不知道招生的消息,我也想考啊!”小伙伴说考试已经结束,鲍蕙荞却坚持“不管怎样,也要试试”。第二天,鲍蕙荞就跟着小伙伴跑到了中央音乐学院设在中央戏剧学院的招生点,找到了主管业务考试的老师。“可能是我的勇气和真诚感动了老师,她们当即决定第二天早晨破例为我一个人举行一次业务考试。”回想起这段经历,鲍蕙荞说,当时没想过能不能考上,一听说可以参加考试就马上回去练琴,第二天一门心思地去考试。“想来我当时还是相当自信的。”第二天在考场,鲍蕙荞弹了两三首曲子,又考了“耳朵”,考试就结束了。下午,主考老师来电话通知鲍蕙荞被正式录取了。从做出报考决定到被正式录取都发生在48小时内,错过了正式考期、没有介绍信、没有文化课考试的鲍蕙荞,就这样被录取了。而这短短的48小时,几乎决定了鲍蕙荞一生的道路和命运。
入学后,鲍蕙荞插班进了少年班的三年级,在主科老师陈比纲的教导和基本乐科老师朱起芸的帮助下,“半路出家”的鲍蕙荞很快进入了“尖子生”的行列,经常有演出机会。1956年,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钢琴比赛的国内选拔赛上,16岁的鲍蕙荞顺利通过第一轮比赛,在第二轮比赛中却因“太嫩”被刷了下来。这更加坚定了她要刻苦练琴的信念,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来练琴,晚上练到半夜也是常事。同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访问天津,鲍蕙荞在为两位总理举行的音乐会上演奏了肖邦的《降b小调谐谑曲》。可想而知,这对当时仅仅是中学生的她来说,是莫大的光荣。1957年,鲍蕙荞凭借全优的成绩被保送到了中央音乐学院本科。
1961年对鲍蕙荞来说,又是难忘的一年。当年鲍蕙荞被指派参加第二届乔治·艾涅斯库国际钢琴比赛的国内选拔,鲍蕙荞和上海音乐学院的洪腾取得了胜利,代表中国去罗马尼亚参加比赛。在到达罗马尼亚之后,练琴
比赛获奖,对于鲍蕙荞来说像是一个新的起点。不久之后,鲍蕙荞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正式参加全国文化课统考后录取的第一个研究生,又在“布拉格之春”钢琴比赛和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两次国内选拔中获胜。但是这两次比赛都因政治形势发生变化而没有去成。在1966年之前,鲍蕙荞的钢琴之路一直顺遂。“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么多奢望,每天就是开开心心弹琴,偶尔比赛没选上或者淘汰了,顶多是哭一鼻子,小失落也会很快过去。总觉得国家给的机会还会有的。”
靠不断学习“自我疗愈”
1968年,鲍蕙荞生下儿子不到三个月时,她这个1966年中央音乐学院
上世纪70年代鲍蕙荞在农村为农民演出现代京剧《红灯记》(钢琴伴唱)
“任何时候都要学习,学点本事,不知道哪天就能用上。”1977年,父亲患脑癌瘫痪在床,鲍蕙荞悉心照顾了三个月,父亲还是离去了。心力憔悴的鲍蕙荞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心跳过速,手脚发抖。即便如此,她还是每天练琴四五个小时,弹了许多新作品。“过去十几年,我失去了太多的宝贵时间。”1985年,鲍蕙荞与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她更加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挚爱的事业中去。“有人觉得心里烦躁的时候就不想练琴,我恰恰相反,痛苦的时候拼命练琴,倒是能从中得到一丝慰藉,心情会逐渐平静下来。有时候连生理上的病痛都减轻了。”
在近20年间,鲍蕙荞从未停止过工作,参加演出、活动,担任评委,办学,一刻也不停歇。只要是对钢琴事业有帮助的事情,需要献计献策的,鲍蕙荞从不推脱,但是跟钢琴关系不大的活动、节目,鲍蕙荞一概不接。
2006年,鲍蕙荞在体检时发现患了乳腺癌。知道患病的消息之后,鲍蕙荞淡定地取消了后面的演出。在进入肿瘤医院检查期间,她上午在医院检查,下午还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照常给学生们上课,甚至连晚上学生独奏会的演出,她也是照常去支持。手术前安排家属签风险告知书的时候,鲍蕙荞从头读到尾,平静地签了字。“既来之则安之,躲不过去就得面对,最坏的结果已经想到了,就感觉没什么好害怕的。”术后八个疗程的化疗期,前半程是呕吐不止,后半程是关节疼得睡不着,鲍蕙荞一声没吭地挺了过去。在接受央视《艺术人生》采访时,鲍蕙荞说,“如果老天爷一定要选一个人得癌症的话,那应该是我,因为我比别人承受力更强,我能扛得过去。”手术后,她练琴少了,也停止了演出。为了不虚度光阴,她开始跟一位老师学习英语。从新概念英语学起,每周都要背几篇课文,鲍蕙荞称之为“自我疗愈”。“以前一直想做的事情,现在总算是有时间做
《华夏琴韵》重燃激情
2016年,鲍蕙荞作为评委会主席,并为之努力了十年的“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停办了。为了尽快遏制失落的情绪,鲍蕙荞觉得必须找到一件能让自己重燃激情的工作。思考过后,她决定在尚能演奏的时候,留下一些自己的琴声。“录什么呢?录300年来的外国经典作品,我想我比不过外国大师。我是中国钢琴家,为什么不录中国作曲家的钢琴作品呢?”做出了决定后,鲍蕙荞开始选曲、练习,想录制的作品
现在的鲍蕙荞,仍然是气质优雅的女性,真丝衬衫、黑色半裙,半高跟鞋。在任何时代她都是最有魅力的钢琴明星,即便被抛掷在时代的漩涡里,几经沉浮,即便经历过那么多身心的创伤、坎坷和病痛,钢琴事业仍是她的精神支柱。也正是因此,鲍蕙荞脸上依然没有太多来自岁月的痕迹,腰板永远挺得直直的,眼神一如既往地坚定从容,思维也依然清晰活络。
在《倾听同行》第一集里,鲍蕙荞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钢琴在你的生命里意味着什么?”各国钢琴家们的回答各异。同样的问题抛给鲍蕙荞时,她说,钢琴已经融入了她的生命。每当她的生命中出现难过的坎儿,或者是病痛难忍时,钢琴永远能给她力量,使她坚信自己一定能走出来。“弹钢琴和做人一样,必须要有韧性,要像弹簧一样能屈能伸。”
-
 微信公众号中国音乐网官方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中国音乐网官方微信公众号 -
 官方邮箱chnmusic@qq.com
官方邮箱chnmusic@qq.com -
 官方微博中国音乐网官方微博
官方微博中国音乐网官方微博 -
 官方微信官方微信:chnmusiccn
官方微信官方微信:chnmusiccn -
 联系客服客服QQ: 2296549528
联系客服客服QQ: 2296549528